(来源: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: 张炜煜 吴爽)

作为国学大家和教育家,张岂之手不释卷,至今仍每天坚持读书、看新闻。他住在清华园的一所老居民楼里,尽管80多岁了,但衣饰向来整洁,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。他身材高大清癯,举止优雅,令人见之忘俗。
他最近在看《朗润琐言: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》并做笔记,每次出去开会都看一点,觉得好的都划了重点号。以有涯人生做无涯探究,张岂之乐在其中。
影响深远的几位老师
张岂之生于1927年。少年时,由于战乱,张岂之就读的学校一再变动。在江苏南通读的小学,在甘肃兰州读了初一、初二,再到陕南城固读初三,后来又到重庆,就读于南开高中。
1946年北大、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和天津复校,并于次年联合招生,张岂之报考了北大哲学系。他还清晰地记得语文作文题目是《学校与社会》,作文中强调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,得了很高的分数;他也不偏科,数学考了60多分,以正取生的身份被录取。
汤用彤先生当年任文学院院长,开出了魏晋玄学、英国经验主义、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。汤先生想让学生知道,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。这种教学方法让张岂之受益终生。张岂之当年听了前三门课并做了详尽的课堂笔记。汤先生不仅看过这些笔记,甚至还亲笔修正了里面的错讹。这些笔记如果现在还在,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。
让张岂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。在“英国经验主义”课堂上,汤用彤先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:洛克如何用经验主义修改了笛卡尔的知识学说?张岂之认真阅读了原文,很快写出了读书笔记,但汤先生认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,即没有注明笛卡尔能够贯彻其知识论的起点:“我思故我在。”青年张岂之辩护道:这些我懂,别人也都懂,所以没必要写出来。”汤先生的教育风格就是娓娓道来。他轻轻地说:要从学生时期养成好习惯,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,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,要处处考虑读者。文章中重要的环节即或众所周知,也不能省略。
贺麟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有效。那时候他开的是“黑格尔哲学”选修课。1948年选读该课的共有5名学生,贺麟先生译出了中文本《小逻辑》,让学生根据原著对中文本“加以校正”或提出问题。其他4人据德文版,张岂之据英文版。平常自学,每周去贺麟先生家里听一次课,大家常常能发生争论。这种教学方法特别有启发性,5人之一的杨祖陶就是这样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。后来,贺麟先生在《小逻辑》译本(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)“引言”中说:1946至1950这一学年内,我在北京大学授“黑格尔哲学”一科,班上有杨宪邦、张岂之、杨祖陶、陈世夫、梅得愚诸同学,并有王太庆、徐家昌二同志参加。上学期我们研读《小逻辑》,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《黑格尔〈逻辑学〉一书摘要》,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,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,作有读书报告。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,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。
上大学的时候,张岂之求学积极主动。有个学期,讲师齐良骥开的选修课《英文哲学名著选读》只有张岂之一个学生选读,但系里并没有因此停开这门课,齐先生也没有提其他要求。结课后齐先生还递给他一张纸条,问自己讲课的不足之处。后来的石峻先生讲课风格不同于齐良骥先生,他热情奔放,随时挥洒,听得人天宽地阔。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湖南乡音较重,语速较快,有些地方学生听不明白。于是张岂之就把听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归纳出来,写短信给石先生请求点拨。石先生有时候留书给张岂之,纸条上会提示阅读时注意哪些问题。他还主动问张岂之需要哪些书,并带他到自己堆满了图书的宿舍让其挑选。张岂之借书后写借条,石先生不要,说你用后还我就是了。师生间这份宝贵的情谊迄今让张岂之感念不已。
一向重视高校教学
1950年,张岂之从北大毕业。毕业以后有两个途径:一是工作,二是继续读书。任继愈先生建议张岂之继续读清华哲学系研究生。任先生还让张岂之星期天去见他:“我带你到清华看看,环境很好,学术气氛也不错。”张岂之一度担心自己考不上,任先生鼓励他好好准备。当年清华大学招了24名研究生,哲学系有3个名额,其中就有张岂之。
随后有消息传出:清华不办文科了,都并到北大去。这让文科学生惶恐不安。好在柳暗花明,天无绝人之路。张岂之的另外一个老师、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派人来找他。1948年张岂之听过他的《中国思想史》专题课,得了80分的成绩。1951年侯先生到西北大学去做校长,想要把在北大听他课的学生带去,这可把张岂之高兴坏了。第一,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,西汉、唐两个盛世都在这里,文化古迹丰富,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好的城市;第二,西周就是在那里兴起的,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;第三,西北大学当时是国立西北大学,前身是西北联合大学,老师当校长,跟着他学,进步会挺大的。就这样,张岂之决心去西北大学。
甫去,侯先生就给了他讲师名义:“你在清华当过研究生,我不给你助教身份。”侯先生强调:讲课的人是讲师,不讲课的人不是讲师。就这样,张岂之第一门课是给法律系调干生讲《逻辑学》。侯先生来听了他一堂课,说原理讲得可以,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,还需要继续努力。
张岂之对教学一向重视。从1952年到1978年,20多年他一直是讲师,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评为教授。
改革开放以来,张岂之担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,后来又当了副校长、校长。这都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不过当校长的时候,他依然没有放弃业务,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《中国思想史》。学生们回忆说:张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时不看原稿,旁征博引,信手拈来,听起来非常过瘾。其实并不是张岂之记性好,而是他重视课堂教学,准备充分,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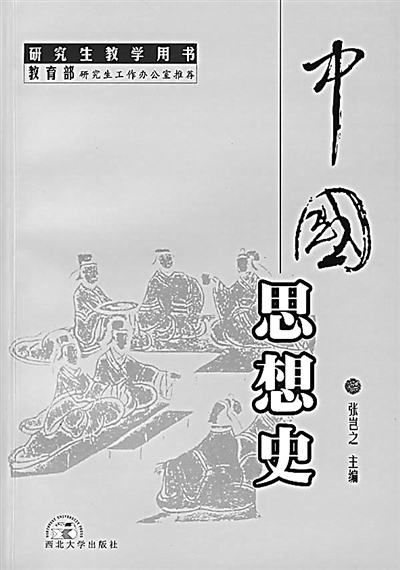
现在高校有重科研、轻教学的倾向,但在张岂之的记忆中,教他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。这对张岂之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。 在科研和编写教材之间,张岂之一直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。没有上级布置,没有申请课题,没有启动经费,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下午,张岂之和几位同仁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归纳出若干原则,之后就开始了《中国思想史》的编写工作。这本由张岂之统稿主编的教材今天依然在大学里使用。2002年,张岂之又主编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《中国思想文化史》,历经4年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社会上一度出现贬低、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,这促使张岂之决心推出适合年轻人阅读的书来。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拟出提纲,又邀请专家,主编了《中国传统文化》一书。该书于1994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,此后又出了插图本和英译本,共印刷十多次,迄今不衰。张岂之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,2002年,他拟出15个专题,以“物质文明”“精神文明”“政治文明”“制度文明”为主线,邀请学术观点相近的专家写出了《中国历史十五讲》一书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销量很不错。作为侯外庐的学生和长期助手,侯外庐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《中国思想通史》,也有张岂之的一份贡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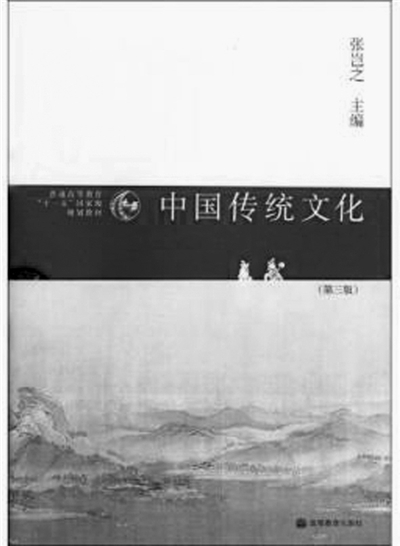

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,张岂之谦虚谨慎,他说,有生之年,在学术研究上要再做一些事,还有新的计划要实现。
(按:文章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7月24号第10版“名流”版,
并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、人民论坛网、人民网、中国教育新闻网等网站)

